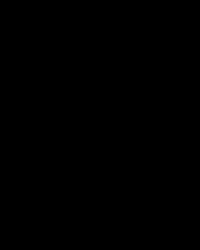云绾宁墨晔小说>王都三十日 > 122第十六日世事如烟烟消上(第2页)
122第十六日世事如烟烟消上(第2页)
他听到“势”字,心中忽然振作:我寒氏一族,自寒浞以降,已经衰败到无人知晓的地步,若非我寒燎苦心经营,何来今日之局面?若说顺势,我寒燎起家之时“势”在何处?!
“譬如道边硕果,旁有恶犬,无视便好。”宾让继续闭着眼睛,缓缓说道。“前人不伸手,只因恶犬旁伺。只须跟随路过便好,若伸手去摘,徒惹是非祸殃。”
恶犬!
那小五便是一条恶犬,我也要灭了你!
我要灭了他!!
我要灭了他!!!
寒燎嘴角不住抖动,眼中精光闪烁。
“数穷不可怕,不知顺势,致剥而终吝才可怕。”宾让闭着眼睛,不知道寒燎此时心中所想,继续道:
“剥有毁灭之象。事不可为,我无新解。”
宾让说完,低眉内视,等寒子问话。
毁灭……硕果……恶犬……寒燎心里不断重复着这几个词,在心中幻化为几个不断闪现的画面:伸手可得的硕果,永不能再见的儿子,可随手灭杀的恶犬……
执念一起,恶从中来,寒燎伸手拔出长剑,指着宾让的头,大声喝道:“顺势而为!尔等不顺我势,不怕我先诛杀了尔等么?!”
“怕,怎么不怕!寒子不能杀觋人,却能杀我。”宾让微微躬身,不卑不亢地对寒燎说:“只是,此卦是寒子亲手所起,只能应在寒子身上,却与让无关。”
寒燎虽迹若疯狂,但也知道此事与宾让无关,一脚踢翻案几,对宾让大喊一声“滚!”。
见宾让依礼慢慢退出房间,寒燎心中一口恶气发不出来,对着案几一顿乱砍,砍得案几木屑乱飞。一边砍,一边喊:“我势诛杀此恶犬,尔安敢乱我心,尔安能乱我心!”
北郭标心痛案几,却不敢上前阻拦,对身旁寒务轻声为难道:“羁舍之物,乃是王室之物……”
寒务知道北郭标的意思,只是盛怒之下寒燎已经杀了计信,他如何会去触这个霉头,苦笑道:“走时依价赔你便是,定不让族尹为难。”
寒燎泄了心头邪火,带着寒望、寒务及另几名族中好手当即出发,由计平带路往前赶。
寒务很委婉的向寒燎说了希望寒子直接回寒地的意思,要寒子不以身犯险。毕竟以寒燎子爵之尊,在这林间野外,不可知的危险太多。况且计五的射术,在这半年中,已经被传得神乎其技,未免让寒务有些担忧。
但寒燎既然知道了计五的行踪,如何肯放手?更何况寒望所言**,即刻动身,计五立即成擒,面具和让国诏书唾手可得。
任寒务说得危险万丈,只是执意不回。说到后来,寒燎发火:“若不是你们奈何不了一个逃奴,何需我亲自履荒郊,穿密林!”
一番话说得寒务几人无法应声。
北郭标拿着寒务赔付的一个铜贝,望向寒燎一行人匆匆离开的背影,又转头愣看着没怎么动过的朝食,挥手对族人说:“撤了,各家分食了吧。”
北郭标将铜贝纳入怀中,一张案几换来一枚铜贝,值!
秋雨止歇,但计平带的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近路,山路崎岖,道路泥泞,寒燎等人走得越来越慢,好在计平似是来过一般,一路却都顺畅。
唯一可虑的事寒燎在半路上开始咳嗽,寒务一直在寒燎身边服侍,知道寒燎近来身子不好,便有些懊恼,悄声对寒望说,要他劝动寒子回去,寒望连连摇头。
寒务已经算是在寒子面前说得上话的,他都没能说动寒子,寒望原本就怂恿寒子亲往擒拿计五,连说自己无法说动。
寒务不得已对寒燎说,是不是休息一阵,计五那边要等到正午启程,时间上尽够。
寒燎暴跳,指着寒务等人鼻子大骂:
“这么多人追杀小五一人,每次还让小五走脱,便是因为有你这等怕与小五对阵之人!”
寒务本是好意,被寒燎破口大骂,脸上青一阵白一阵,等寒燎骂完,默默收拾了,跟在计平身后出发。
在林子里,他们看到一具被野兽咬得已经没了人样的尸体。
计平默默从尸体便走过,其他人也没有停留,寒燎走过时却多看了几眼,他想到寒布,自己的儿子也同样死在郊野,在一整晚暴尸野外,而他甚至没看到儿子最后一面。
之前他很悲哀,没能见寒布最后一面,而眼前被野兽咬得零落的尸体,寒燎忽然很庆幸自己没看到儿子死去时的样子。
他见过太多的死者,但看到这具他绝不可能认识的尸体,就这么狰狞地躺在地上的时候,寒燎想起清晨觋人说的“事不可为”,从心底生出一种悲哀与无助。
“埋了他。”之前绝不肯休息的寒燎吩咐手下。
这个命令耽误了他们不少时间。
寒燎坐在一块兽皮上,痴痴地看几个人忙碌着。
寒望、寒务浅浅地挖了一个坑,把散落的尸身放了进去。
寒燎咳嗽着缓缓走过去,从身上摸出一块玉,丢进坑里,又叫寒务丢了几枚碎铜,捧了一抔土,撒在坑里。